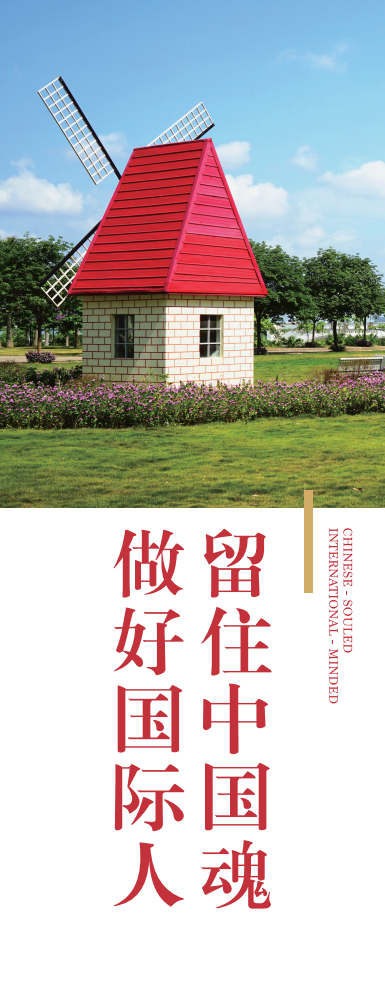2011年,记者蒋昕捷的一篇《围剿地沟油》点燃了整个互联网,也点燃了广西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——冯源。学校优秀毕业生冯源,现为广西日报传媒集团《南国早报》的一线记者,毕业以来手握数十份获奖作品。“新闻事业是累的,但是我确实是为了理想去的,那也就不那么累了。”

(图1:冯源(右一)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)
“千里挑一”
“什么是不可能,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要去试试。”
2018年,冯源来到了广西外国语学院,实现他抱负的时候到了——想要成为蒋昕捷那样为人民发声的人。
2019年的第一次暑期实习,冯源去了北海日报,从采访小白到华丽蜕变,他经历了前辈一次次的训斥,深夜一次次的修改采访提纲,所谓挫折使人成长,便是如此。
2020年,第二次实习他已经是“小老师”了,他带新的实习生走出学校。新的实习生在旁观摩他的采访操作,还不断问询:“冯源学长这个要怎么做……”这是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骄傲。
毕业以后冯源决心要做一名记者。2022年,他在南宁日报社500份简历中脱颖而出。2024年他又在广西日报1200份简历中,再次脱颖而出进入笔试、面试等环节,最终被广西日报录取。单从比例来说,这个难度就是妥妥的“千里挑一”。
“苦其心志”
冯源最初踏进校门的时候,有些迷茫不安。那段时间他总是不知道应该干什么,“课也上了,作业也做了,但总觉得不够。”这种不安感让他晚上时时失眠,黑眼圈日益加重。没有了高中明确的目标,他有些迷茫,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努力,朝着哪里努力。
第一次实习经历,让他的目标清晰起来。当时,冯源是新闻1803班唯一“听劝”,利用大一暑假前往媒体实习的学生。去实习的第一天,带教的陆威记者并没有直接就让他自己去采访,而是让其一直跟在旁边观摩自己采访。直到采访结束陆威才和他说写一篇通讯。“我当时觉得这就是我表现的机会。”冯源立刻回宿舍,写好了通讯发给带教老师,“当时带教没说什么,只是把我的作业发了回来。”冯源一点开打回来的通讯,整篇通讯只有一处是没有标成红色的,每个标红旁都有批注,其中最多的批语就是“口语化,不够精简。”
“当时真的天塌了,怎么会这么惨。”冯源当时盯着文档看了很久,他把每个批语都看了不止一遍,他想过反驳“不至于吧,怎么会这样。”但是事实就是如此,就是写得这么差。
“改!”“不要自我内耗,内耗不如行动。”冯源内心想就不带怕的,那天他去查看了带教发过的文章,钻研了两个小时,一字一句和自己文章做对比。“我确实还有太多不足了,实践果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”
改到了凌晨两点,他还是没有什么睡意,要不是明天还有任务,他说他能看着这篇通讯到第二天早上。第二天的作业如期而至,这一次作业上交以后,虽然还是被打了回来,但是标红就只有三句话。
“劳其筋骨”
成为一名正式记者后的冯源说:“我记得有一次要在两天时间内写完13篇稿子。那时候就心无旁骛关在房里写了两天两夜。”
在一次出任务回来以后,冯源直接躺在了椅子上,根本提不起一点力气。他在过去的24小时里,跟同事轮换着开了13个小时的车。但是开车并不是结束,到了目标地点以后,他还要打起精神,拿起相机走进各家各户,去采访、去了解事实。
背上全都是晒伤,没被衣服遮住的地方呈现了暗红色,一摸上去就是火辣辣的痛,时间紧任务重,他没时间在意这些,他得到地方去倾听民众的声音,这是他的职责。
在村庄里采访,他要走的路不可谓不多,那天他记得微信步数是4万多步,第二名才8000步。脚上起了个水泡,走到后面,甚至水泡都被磨破了。他回家一看袜子上已经有血渍了。
这样的活动在记者生涯中还有很多,他总是走在第一线,那个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,随时准备采写新闻的大男孩。
“我要用脚去丈量新闻。”他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

(图2:冯源在采访地立地成稿)
彼时彼刻,正如此时此刻
阔别学校两年的他,还是在各位“老前辈”校友面前的小伙子,在校友介绍的过程中他还带着一丝腼腆,说的话也非常务实,“欢迎学弟学妹来我们这实习。”他也胖了30斤,他看着两年后的自己,自己也笑了,同学都笑着说:“两年前的冯源去哪了。”
冯源估计也想不到5年前那个瘦小伙,会变成“婴儿肥”,5年前那个有些迷茫的小伙子在写第一篇采访稿时,也不会想到5年后的现在,他也是别人笔下的新闻人物。彼时彼刻,正如此时此刻。